前几天,和一位诗人朋友喝茶闲聊。
那是一个40多度的炎热下午,我们约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。我俩几乎同时到达,落座,喝上一口冰水,彼此相视,能互相看到对方满头的汗。
话题开始轻松,逐渐沉重。诗人年逾五旬,大学时期曾出过诗集。那是他的第一个诗歌时代,也是为他积攒了最初声望的阶段;而后互联网兴起,他是最早一批“著名网络诗人”之一。此言非虚,那时我是他的读者,他的大名深印在我心中。但热闹了几年后,他停止了写诗。这个暂停键按得太久,从他一脸骄傲的朝气始,到如今的他已是一脸平静止——他又开始写诗了。
我问为什么当年停下笔?他的答案是,觉得当时的自己,虽然能算一个不错的诗人,但掂量掂量,恐怕也到不了顶尖。这是一个年轻人不能接受的自我审判,于是他给自己判决终止写作。
那为什么又开始写诗了呢?诗人说,对抗死亡吧。
这话听着莫测高深,但我懂。同为中年人,生活中已经开始不断有人告别。死亡不再是遥远且不合时宜的话题,反而像一张厄运彩票,鬼知道下一个中奖的会是谁?
在这样的情境下,写作成了一种有仪式感的东西,效果接近于对自己进行心灵按摩。当一个喜欢文字的人和死亡越来越接近,就会对世间的一切加倍敏感,想把这些沧桑写下来。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写过,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野里遭遇到那种宏大壮丽的落日,男主人公沐浴其中,突然像开了天眼,回想起人生种种。我觉得,写作的冲动就是类似这种感觉。
说完月亮,回到六便士的问题。眼下,喝喝咖啡聊聊天,是最舒服的消遣。互相也都“识相”,能用特价券就用特价券。以前,嘲笑老外一瓶啤酒就可以在酒吧泡一天,现在我们也总是一杯美式在咖啡店消磨掉一整个炎热的下午。
我们互相打探,现在各自靠什么营生,答案殊途同归,“不想卷”。悠长岁月里,如果没有拼命赚钱的想法,每天把时间交给文字和有限的几个朋友,生活不免就会进入内省。他说,也不过五六年前,明明还有梦,还想着赚一大笔钱,干一个好企业,但转眼间梦就碎了,不如返回经营自己内心的小世界。
说白了,外头的精彩和你我无关,写作没啥成本,是属于一个人的精彩,所以缩着头,努力写点。
写作很有效。诗人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技法,并且坚信是第一流的。我知道,就算是第二流的,他照样还是会写下去。中年人内心消停平静,往往始于接受自己真的不是个天才。
聊了两个多小时,咖啡杯里早干了,又喝了好几杯柠檬水,我们告别。走出咖啡店,他向东,我往西,但顶着一样的烈日。不用多久,我们都会一样的满头大汗,狼狈不堪。
我三十来岁时,有人问怎么才算一个优质的四十岁大叔,我欣然回答:第一,要有钱。不需要很多,但起码应该让你在四十岁,跟别人谈点人生梦想时,不会因为太穷而脸红。第二,要有趣。你积攒了那么多人生经验,看了那么多世界,总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?第三,要有品。一是人品,二是品味。不求是圣人,但总得有担当;不求是贵族,但总归让人看上去干净整齐有腔调。
十年过去了,我好像并没有变得更优质,但好在还有提笔的勇气。诗人中年重新写诗的理由如此深刻,于我却简单。我想变好,想做一个优质大叔。写作能让生活狼狈的自己,自我感觉优质点。
此时不动笔,就怕来不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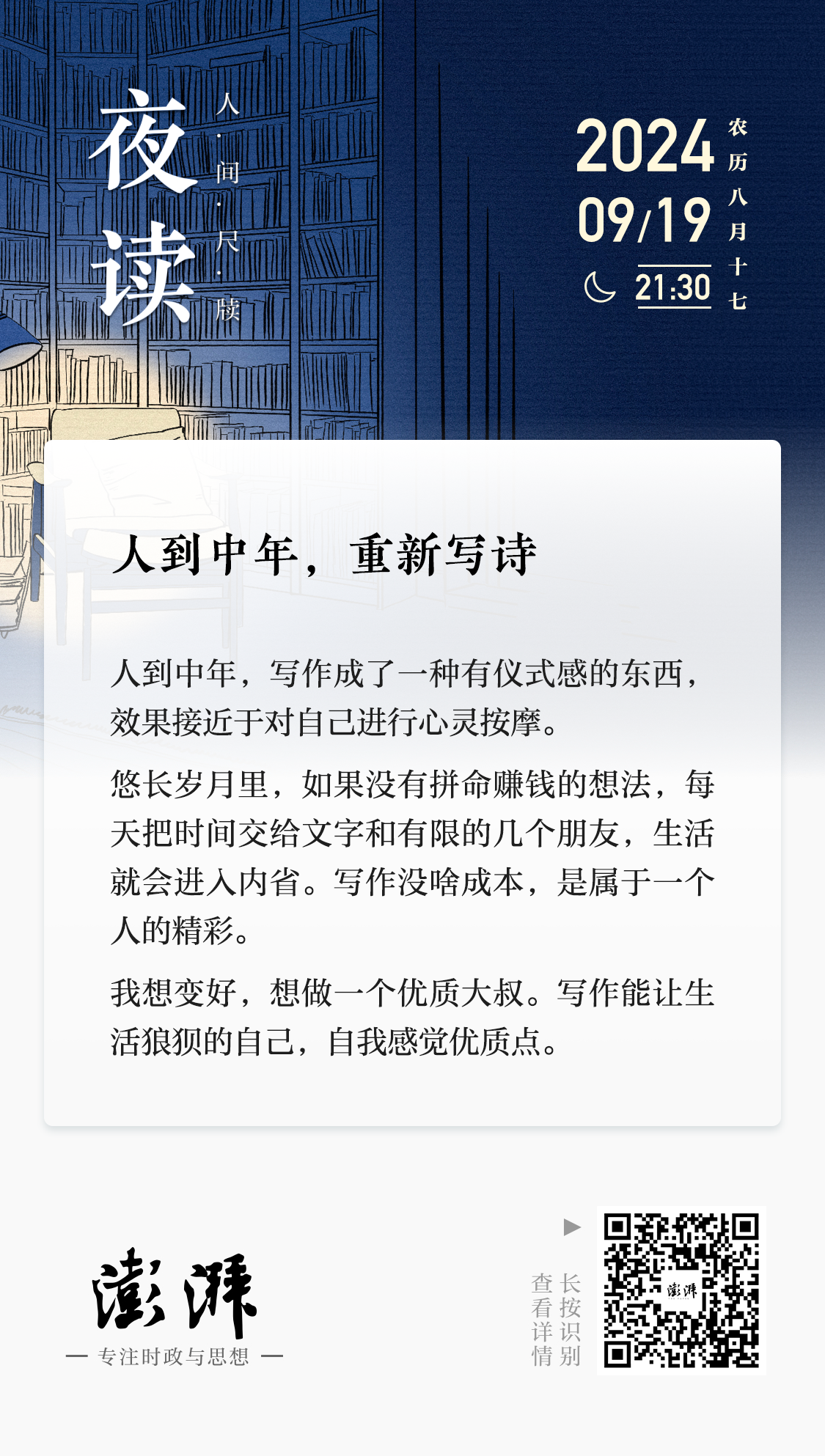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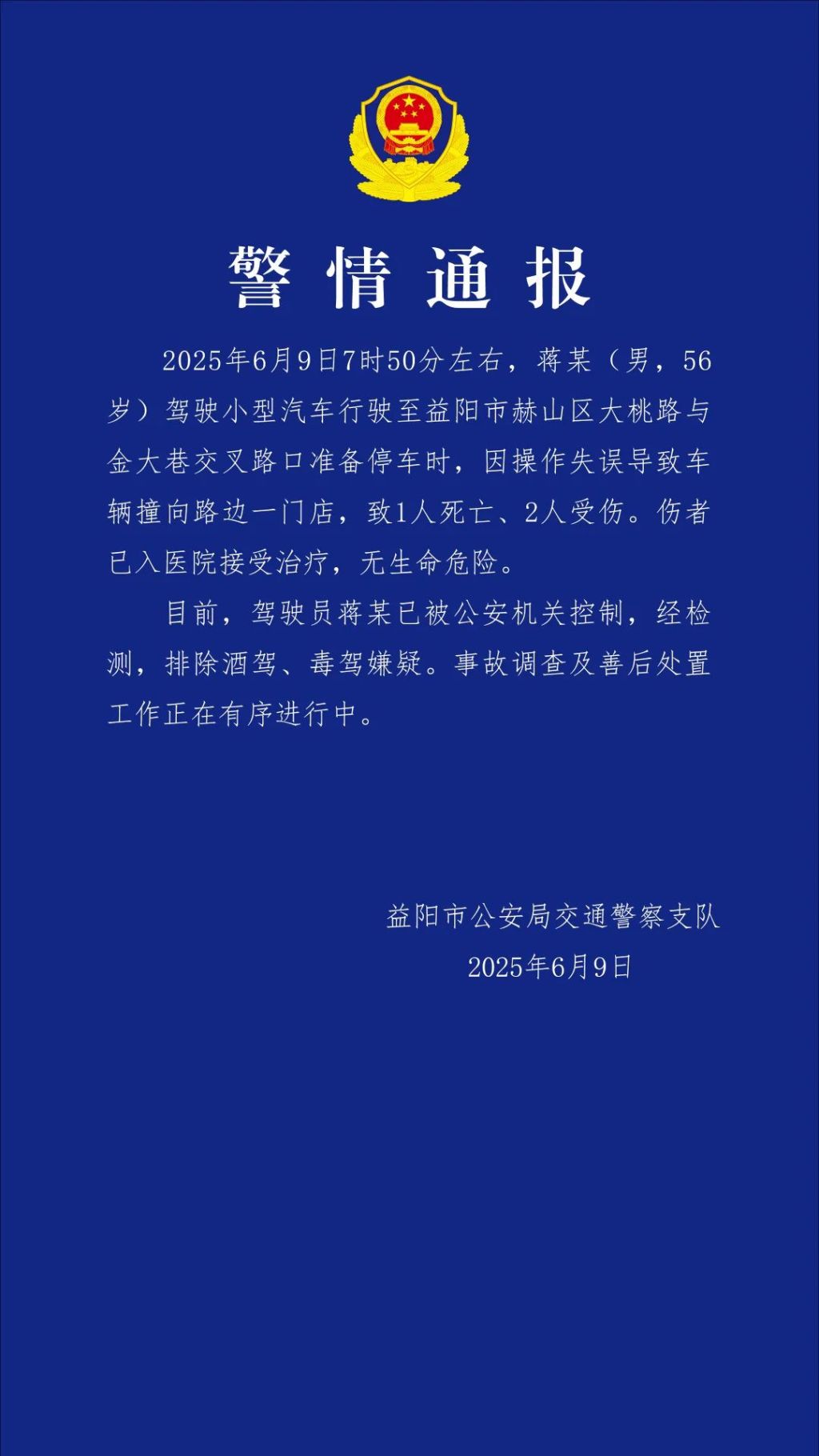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